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he CPC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s “Kafting Gorge” theory in its journe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and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i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for reality. Design/Methodology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ethod,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Marx’s “Kafting Gorge” theory, then analyz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CPC’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theory, and finally show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Findings The theory of “Kafting Gorge” has broad and narrow meaning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inherited Marx’s broad sense “Kafting Gorge” theory from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the CPC has also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spanning the capitalist stage 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world situ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entury long journey of the CPC to the theory of “Kafting Gorge” has proved the scientific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mote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lso provided a Chinese progra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and other countr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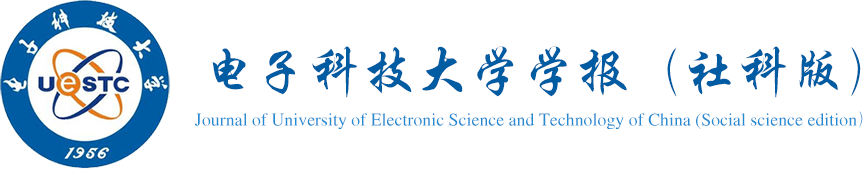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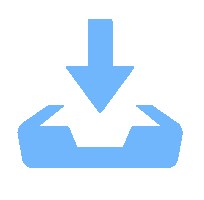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