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Network Ideology in Recent Years: Focus and Prospect
-
摘要: 聚焦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传播机制以及治理策略等基本问题,梳理了近年来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成果,阐述了已有研究的角度、观点和方法并归纳了会通和分歧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深化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方向,包括:网络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研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中国道路、理论和话语研究。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leadership, discourse power,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other basic issues of network ideology,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network ideology in recent years, expounded the perspective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summarized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n this basi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n network ideology is put forward, including: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network ideology; study on modernization of network ideologic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road, theory and discourse of network ideological governance.
-
Keywords:
- network ideology /
- leadership /
- discourse power /
-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
- governance
-
随着互联网深度嵌入生产和生活进而引起人们接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不同程度的变迁,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网络强国”等理念的提出,网络意识形态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研究中的热点。学者聚焦领导权、话语权、传播机制和治理对策等热点问题,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视角对网络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本文对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深化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建议。
一、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
葛兰西最早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他认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尼科斯•普兰查斯、雷蒙•阿隆、李普塞特等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
目前,学者在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界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郑永廷从阶级属性的角度指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夺取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本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遵循一定的国家权力分配管理原则,以国家机器(包括暴力机器和非暴力机器)为保障,运用计划、决策、组织、领导和控制等国家职能,通过制定意识形态政策、设立意识形态机构、配备意识形态管理人员,占有支配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国家权力”[2]。这种观点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性,将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解为一定阶级运用国家职能实现阶级意志表达的权力。程竹汝、郭燕来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指出:“所谓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主导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非强制影响力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赞同从而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3]。这种观点突出了意识形态生成过程的社会参与性,强调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具有自发性和非强制性。卢旭东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从规范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指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4],强调产生认同力的非强制性。以上两种观点分别从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角度对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了界定,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揭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性,后者则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生成的自发性。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由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扩展,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综合学者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不同角度的阐释,把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和生成机制结合起来,将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界定为:基于信息化、符号化的网络场域,以理论的科学性和伦理的正义性为基础,以形成具有普遍认同的网络价值准则和维护政党、集团或阶层的政治合法性为目标,以价值引领、制度规制、权威塑造为手段,通过网络媒介有目的地引导公民将分散的思想和观念自觉地融入政党、集团或阶层意志的力量和权威。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是网络空间中价值观念的引领和合法性权威的塑造,内在生成逻辑是思想生产→价值认同→权威服从。思想生产是基础,即生产系统化、理论化的网络思想体系,并赋予这种思想体系以普遍的形式;价值认同是灵魂,即将网民的意志统一到本集团、阶层或政党的意志上来,形成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的理论体系”[5],产生价值引导力;权威服从是目标,即思想体系、价值体系转化为信仰体系,影响网民的认知、审美和思维习惯。
与传统意识形态领导权相比,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面临的环境具有更大风险性。因为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具有强自发性,众多“栖居”在网络空间中的网民代表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并随时发声,使得网络空间成为各种思潮及价值观的“收容所” “角逐场”和“舞台”,价值混乱、价值失序成为网络空间存在生态的重要特征。其二,领导权的本质体现具有隐蔽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传统意义上它的实现主要依赖科层制的行政体系和法制化的政策条令。在网络空间中,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更多的是通过多样化的、能够让网民接受的柔性方式实现的,政令、法令等直接体现阶级性的刚性约束弱化。其三,领导权的实现方式呈现扁平化。它不再是传统的、单一的自上而下、层层灌输的梯级传导方式,而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由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集团主导,网络大V、意见领袖、普通网民多元参与。
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在网络场域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强化理论创新,夯实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根基。兼具科学性和真理性且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石,否则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成了无源之水。要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方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在坚持基本立场、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立足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解答网络空间中人们提出和反映的现实问题及思想困惑,体现理论的强大感召力和说服力。(2)突出价值引领,形成网络意识形态价值认同。“意识形态不是某种特殊的信仰或一套信仰,而是大多数人共同的世界观”[6]。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社会力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吸引力,在网络空间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和稳定的文化心理。(3)强化制度构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安全。有学者从“微空间”的价值生态出发,提出要尽快完善规章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建立起舆情反馈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提供一个相对有序的信息环境[7]。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面对西方国家在网络上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有学者提出构建“网络信息的预警机制、网络舆论的引导机制、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卫机制、红色文化的抵御机制”[8]。
二、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的网络空间,争夺话语权成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话语“作为交流和社会互动的主要工具,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9],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本和话语再现的”[10]。在阶级社会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会通过某种特定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体现权力属性和权威特征。首次将“话语权”作为独立概念提出的是法国哲学家福柯,他将“话语”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指出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交际工具,更是一种权力。西方学者厄尼斯特•拉克劳、尚塔尔•墨菲、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也从多个角度论及话语权问题。
对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目前学界的研究较少,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两类。一类将话语权等同于“话语权力”,强调话语权的阶级性、统治性和主导性。如郑元景指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主要是指在网络社会中,权势集团、信息传播主体依据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仅仅满足于通过网络媒体享有发声的自由和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权力,更在于通过虚拟世界中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支配,获取潜在的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依靠权力体系压制其他话语的表达,使隐含主流价值的话语通过网络平台渗透到大众中,从而引导和掌控现实社会思想舆论的权力”[11]。这种观点强调执政党、统治集团或者信息传播主体作为网络空间话语的制造者,借助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实现对思想舆论的掌控和支配,以体现阶级或阶层意志。另外一类观点认为话语权既包括话语权力—支配话语的能力,也包括话语权利—言说的资格。在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相互融合、渗透的背景下,执政党、统治集团或公民在网络场域中均享有发声的资格,均具备支配话语的能力。如黄冬霞认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在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虚拟个体与现实个体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网民在网络场域中通过网络实践活动所逐步构建的、以价值观念为核心内容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总和”[12]。本文更倾向于后面一种观点,认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一方面具有阶级性和权威性,是政治权力在话语塑造、话语表达方面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也具有平等性和平民性,是对传统金字塔式话语权力结构的重塑,只有将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方能更好地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本质。
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相比,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新的特征。有学者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要素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由话语环体(在什么环境中说)、话语主体(谁来说)、话语载体(用什么说)和话语客体(对谁说)四部分构成。据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征被概括为:“环体由现实世界转向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结合,主体由国家垄断信息转向网络信息多元,客体的认同方式由外界灌输为主转向自我选择为主,载体也由唯一性转向多样性”[13]。这种表述具有结构主义的特征,分类区分,简洁明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整体主义的关注,即无法说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话语表达方式及功能实现方面的优势和风险;只是从表象上总结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要素的“四个转向”特征,没有进一步分析出现“四个转向”的动力源;强调“四个转向”,具有非此即彼的机械主义思维缺陷,表达的绝对化掩盖了事实本身。还有学者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点概括为四个统一,即:“技术性与人文性相统一” “私人性与公共性相统一” “单一性与跨界性相统一”以及“聚合性与离散性相统一”[12]。这种表述具有定性分析的特征,注重总体性描述,存在的问题是过于抽象化的表述无法更直观、更明确地说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区别。比如单一性与跨界性相统一问题。一方面,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同样必须有指导思想,并且在社会实践中以一元指导思想整合多元意识形态,这同样体现出单一性的特征。另外,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更多地依托政治权力,这种单一性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另一方面,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在表达和传播过程中同样会根据不同的话语环境和文化背景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不同文化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扩大意识形态话语在不同文化间的影响力,这同样表现出一定的跨界性特征,只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做出相应调整的时间跨度较长而已。
提升网络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须在准确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新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路径。学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1)话语内容。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要体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对于网民普遍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工作者应主动在网络上设置相关议题,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嵌入其中,形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聚焦、生长、发展的‘圆心’”[14]。在分析议题时,应该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及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在“理论掌握群众”中产生“物质力量”,增强话语的时代生命力。(2)话语传播。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不仅仅是靠话语内容的现实吸引力,还要依赖话语的传播力。其一,在传播模式上,由偏重于“自说自话”、单向灌输,转向基于尊重受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考虑网民利益诉求与接收习惯的双向互动。其二,在传播渠道上,要打破过于单一化、均一化的局面,注重传播的“差异化、分众化”[15]。其三,在传播形式上,要注重语言表达形式的创新。“意识形态只有与语言联系起来才有意义”[16],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上的争夺主要就是语言和符号在意义生成上的争夺。以网络语言为切入点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能够贴近时代要求和受众的接受心理,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影响力和实效性。(3)信息监控。网络信息突发性强、覆盖面广、传播快,如果处理不够及时,可能会发生政治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因此,必须:“通过建立网络安全监控和分析评估机制,增强网络安全把控和态势感知能力;通过建立大数据语言研判和情报共享机制,增强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能力;通过建立网络行为动态捕捉和网络安全危机处理机制,增强威胁防范和危机处理能力”[17]。总体而言,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需要三方面协同推进,其中话语内容是核心,话语传播是手段,信息监控是保障。
三、 新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机制
在互联网时代,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新媒体带来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载体和方式的变革。如何应对这一变化,构建起适宜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机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大众体验机制。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跨越了时空障碍,实现了生产主体的多元化、输送传达的即时性、覆盖范围的广泛性。社会个体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共享者,也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其主体性得以张扬。一方面,他们只需借助手机、电脑等终端,就可以接收到缤纷芜杂的各类信息,并在政治判断、价值选择和德性修养等方面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虚拟空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影响着某个场域、圈子中社会个体的政治判断、价值选择和德性养成。虚拟空间的这种主体性更多地表现为“体验主体”,也即是“人们通过虚拟空间去体验自我”,相应地,“虚拟空间中意识形态传播要配合人们这种体验式的生存状态”,构建起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大众体验机制[18]。具体而言,一是构建生活化的体验机制。把握新媒体信息传播规律,充分发掘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上引起网民关注的生活热点问题,找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结合点或契合点”[19],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核心价值与人们核心利益和价值诉求的统一。二是构建通俗化的体验机制。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亲和力,“让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了信,产生情感共鸣和内心认同”[20]。三是构建感性化的体验机制。新媒体时代,理性至上、以文字为载体的逻辑化、系统化的信息编辑和传播方式逐渐让位于感性体验为主的,以虚拟的图像、音频为载体的信息编辑和传播方式。普通大众可以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中并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运用音频、动画、视频、H5页面、VR(虚拟现实)等,“把理论形式的意识形态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意义指涉,以感性形式呈现出来,形成感知效应”[21]。这样可以弥补意识形态宣传过于理论化、抽象化的不足,也契合了网民接受信息时的“情绪化判断、实用性心理以及娱乐性心态”[22]。
其二,交互传播机制。在传统媒体格局下,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权威组织自上而下、由点到面的单向进行。自媒体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界限,“多元的传播通道,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去中心、去权威的非线性交互传播模式”,颠覆了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之间自上而下的线性传播关系,信息在“传” “受”主体之间可以“水平流动”,实现“平面化价值沟通和信息传播”[23]。要适应意识形态传播格局的新变化,一方面,要整合意识形态传播资源,搭建信息交互传播平台,实现媒体之间、媒体与大众之间的互动。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平台的宣传作用,拓展大众的参与渠道和互动范围。例如,微博平台的转发功能实现了信息的多级流动,热门话题、最新信息的推荐功能实现了信息跨人际关系网络的传播,这无疑有助于增强网民的信息传播能力,激发网民的参与热情,增进意识形态在大众之间更快和更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传统媒介与‘微媒介’的‘媒介融合’,打破各大舆论场之间的媒介隔阂,实现各大舆论场之间的互动融通”[7]。要将新媒体传播的即时互动性与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结合起来,实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信息的及时共享、融合、互补,形成良性循环。
其三,舆论引导机制。新媒体一方面拓展了网民参与舆论表达的空间,实现了舆论发声的多渠道,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因为网络会产生“孤立风险的放大效应”[24]。执政党要因势利导应对这种情况,必须构建起良好的舆论引导机制。根据学者的研究,一方面要用好权威媒体,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在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场中,权威媒体首先要善于收集网络场域中的舆论热点和焦点,明确网民关切什么、困惑什么、表达什么。其次,权威媒体要及时回应,通过专业且严谨的调查、分析,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抢占传播主动权,掌握舆论话语权。最后,权威媒体在其新媒体平台上主动设置相关议题,“根据用户的接受习惯对传统主流媒体生产的内容进行个性化表达,使其内容具有用户黏着度”[25],吸引更多新媒体平台转载,扩大影响范围,引导舆论走向。总之,既要通过“深度报道”以及“新闻评论”,突出传统主流媒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优势,也要发挥新媒体平台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规模优势,二者“互相呼应与支撑,共同作用于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论”[26]。另一方面要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发挥其桥梁和纽带作用。根据“两级传播”学说,信息或观点往往由大众媒介传递给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传递给其他不太活跃的受众,故民间意见领袖在意见表达和舆论引导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尤其是拥有庞大粉丝、引领舆论走向、深谙传播技巧的网络意见领袖,他们通过共享信息、意见表达以及评论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要把握意见领袖群体在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中的角色定位,通过“加强对‘意见领袖’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搭建和网络‘意见领袖’的沟通平台、注重特殊背景的网络‘意见领袖’、培养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网络‘意见领袖’”[27]等措施,发挥其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助推器”作用。
四、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策略
在复杂的网络舆论场中,每天各类话题刷新着热搜榜,各种思潮冲击着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面对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以及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所带来的网络监管的复杂性、风险性和艰巨性,如何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场上的主动权成为执政党关注的重大问题。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模式和原则。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治理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它既具有传统意识形态治理的一般性规定,也具有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特殊性规定。政党或者集团要根据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生成和传播规律,在治理目标、模式和原则等方面做调适性改变。如有学者提出,中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是:“对内通过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辩护和价值观教育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达成网民价值共识,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共同体’;对外通过批判揭示‘西化’ ‘分化’的网络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免疫力,实现国家、社会与网民同向同行,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8]。针对新媒体时代信息交互传播、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等特征,有学者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概括为“协同化” “扁平化”和“智能化”[29]。“协同化”治理即是指各意识形态治理主体在价值判断上要保持一致,在数据方面要实现共享;“扁平化”治理即是实现党政机关和普通大众的直接对话,减少中间层级;“智能化”治理即是利用先进网络技术提升治理效率。亦有学者总结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原则,观点有所差异。有“五原则说”,包括两种观点,即:“一元主导与多元共治相统一、以德治理与依法治理相统一、主流引导与兼容并包相统一、系统治理与源头治理相统一、积极主动与联合融动相统一”[30],以及“主动出击、包容引导、渗透融合、疏堵相伴、软硬兼施”[31]。还有“四原则说”,即“知己知彼、高度警觉;积极应对、疏堵结合;遵循规律、寓教于乐;与时俱进、着力创新”[32]。“五原则说”和“四原则说”尽管表述不同,但内涵大同小异,都体现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活力”和“有序”相结合的原则,都融入了法治化、协同化、柔性化的治理理念。
二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体系建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一项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具体而言,包括:其一,健全法律法规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依法治网既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性基础”,也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先决性条件”[33]。要不断完善网络信息发布、传播及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网络社交平台群组管理者、账号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打造全方位、多层次、高标准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制度化和规范化治理水平。其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明确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各主体、各部分的职责,健全不同主体、部门、平台等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统筹规划、合理分配资源。既发挥“网民组织的自律”,强化“网络社会主体的自我管理”,也发挥“网民组织的互律”,加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同时还要发挥“政府在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34]。其三,打造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人才队伍体系。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水平,必须汇聚人才资源,以“‘层次分明’ ‘数质合一’为路向打造网络空间人才队伍体系”[35]。要广泛吸纳网络舆情分析、意识形态治理政策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运维、网络媒体运营等领域的骨干力量,培养他们的网络意识形态信息辨析、提炼及研判能力。
三是大数据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云计算的广泛应用,将整个社会带入了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动态的数据体系、多样的数据类型和巨大的数据价值是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海量数据的储存、分类、挖掘和筛选。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36]。大数据技术一方面能够“从人们在社交网站无意中留下的数据中识别背后的行为模式”[37],另外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扩展相互关联的数据集和分析工具来加强监控”[38],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方法。有学者将大数据技术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领域的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主动引领,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话语权;精准识别,切实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针对性;整体治理,着力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科学性”[39]。也即是说,发挥大数据技术快速的数据捕捉和数据处理能力,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数据统计样本,然后对海量数据进行精准高效的分类整理,并对相互关联的数据集进行比对以完成网络意识形态现状的分析以及风险和趋势的预测,避免“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
五、 展望
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学者围绕领导权、话语权、传播机制和治理对策等问题展开的探索,为我们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基本问题、深化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方法论参考。未来需要深化研究的内容包括:
一是网络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并非简单的“网络+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网络化”,它是互联网技术嵌入意识形态引起的意识形态存在样态、表达方式和传播渠道的“革命性”再造,是意识形态治理理念、方式和方法的“颠覆性”创新。不能片面地将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等同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研究,亦不能等同于“网络意识形态技术”研究,应该从互联网的“技术秉性、社会秉性与政治秉性”[40]出发,加强基本理论研究。具体而言,包括: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范畴及相关概念辨析;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基础、方法;网络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表现方式和发展趋势;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学术史的梳理;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式新表述等。领导权和话语权是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两大基础领域,深化它们的研究需要聚焦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对传统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的重构和再造之处,分析国家总体安全观下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的“主权特征”及实现方式。同时,要拓展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研究的学科视野,整合多学科研究力量。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研究“仅停留在一般性论述上,缺乏系统多角度理论阐释,可以综合传播学、心理学、应用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研究”[41]。这虽然是在总结近五年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提出的观点,但对于未来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的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二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网络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包含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把握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国家治理规律和网络技术发展趋势,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民主化、协同化、制度化和信息化,进而实现从传统意识形态监管到现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转变。其中,民主化是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它要求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体现人民意志和主体地位,使各治理主体有序参与并充分发挥各自潜能;协同化是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它要求内部各子系统、子要素相互衔接、高效运转,产生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协同效应,形成各主体共同发力,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信息内容、平台终端、人才队伍共享融通的多元共治格局;制度化是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举措,它要求构建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规范化;信息化是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它要求通过信息技术降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益。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不同于“管理”或者“管控”,它是未来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问题。
以数据获取手段和处理技术及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为主要内容的大数据技术,引起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的变革,成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研究的热点。目前,学者关于大数据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方面的研究呈现的重要特点是:过多关注大数据技术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利好方面,忽略了大数据技术用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风险和挑战;过多关注技术因素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作用,忽略了技术背后人为因素的复杂性影响。未来应重点关注的是:其一,“大数据污染”和“大数据泄露”引致的“数据失真”和“数据风险”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其二,海量数据背后呈现的意识形态信息的筛选规则;其三,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中人为主观性的影响及控制;其四,“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及蕴含意识形态信息的研判。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新媒体平台,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文本、图片、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如何从感性化、碎片化、价值密度低的非结构化数据中挖掘蕴含的“有用信息”,揭示出相关的意识形态符号,既是技术研究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三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中国道路、理论和话语研究。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旧时代一切颠倒的思想体系展开批判,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2]。这句话深刻地揭示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属性,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后来,在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认识到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与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并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资本论》等论著以及系列经济学手稿中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超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设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等概念,并对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了初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到重要位置,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稳定的工作机制、方式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并深度嵌入国家和公民的生活,引起执政党执政理政和公民参政议政方式的巨大变革,如何适应互联网发展要求、巩固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成为无产阶级执政党思考的重大课题。面对网络空间中各种思潮交流碰撞、各种思想交汇交锋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继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借鉴其他国家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把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一般性规律,确立了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内在逻辑、价值取向和实现路径,取得了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历史性成就。着眼于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历程及蕴含的中国价值、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中国逻辑和中国范式;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雷雨, 姜丽, 张跌,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 郑永廷, 任志锋.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研究[J]. 教学与研究, 2013(7): 46-51. 程竹汝, 郭燕来. 思想自由与政治伦理: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几个问题[J]. 科学社会主义, 2012(2): 31-34. 卢旭东.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 理论研究, 2013(4): 71-74. 刘伟.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生产思想及其现实逻辑[J]. 社会主义研究, 2018(1): 24-29. CARMINES E G, D'AMICO N J. The new look in political ideology research[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5(1): 205-216.
鲍宗豪, 刘海辉. " 微空间”价值失序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J]. 思想理论教育, 2018(4): 82-86. 杨文华, 何翘楚.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M].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7. MUNISHI S.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language policy of Albanian language[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2018, 8(2): 125-132.
DIJK T A. Politics, ideology, and discourse[J].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2006(2): 728-740.
郑元景. 当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迁与重构[J]. 社会科学辑刊, 2015(6): 52-56. 黄冬霞.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D].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17. 曾长秋, 曹挹芬. 网络环境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特点[J]. 学习论坛, 2015(6): 47-50. 陈娜. 论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重维度[J]. 网络思政, 2017(6): 75-81. 魏建克, 张月清. 中国共产党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与传播[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2): 30-34. BROWN K.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deology[J].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2,10(2): 52-68.
邓验, 张苾莹. 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逻辑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1): 52-56. 王涛, 姚崇. 网络虚拟空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及其建设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2): 99-109. 刘世衡. 自媒体领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策略[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4): 42-45. 邢晓红. 新媒体境遇下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6): 11-18. 李海, 范树成. 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新机制的建构[J]. 求实, 2014(7): 46-49. 谢玉进, 赵玉枝.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矛盾与优化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18(8): 75-80. 雷洋. 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两个转变—从大众化和感性化趋势性变化说起[J]. 新闻爱好者, 2017(10): 9-13. SHAH D, ZAMAN T R. Rumors in a network: Who’s the culprit?[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2011, 57(8): 5163-5181.
计永超, 刘莲莲. 新闻舆论引导力: 理论渊源、现实依据与提升路径[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9): 15-26. 张晓月.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责任及其路径优化[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2): 93-97. 候新立. 网络政治化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16(11): 161-173. 朱丽萍, 张林, 蒲清平. 网络拟态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24(2): 166-174. 郑元景. 大数据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治理策略[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6(5): 17-22. 苗国厚. 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D].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17. 张晓丽. 论网络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1(5): 41-43. 张志辉. 网络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0. 史献芝.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路径[J]. 探索, 2018(4): 172-178. 唐登蕓, 吴满意. 网民问题: 网络社会治理的切入点[J]. 求实, 2017(9): 56-68. 王永贵, 岳爱武. 着力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4): 1-8. 尤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 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李黎, 郭官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DIJCK J. Datafication, dataism and dataveillance: Big data between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ideology[J].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4, 12(2): 197-208.
LYON D. Surveillance, snowden, and big data: Capacities, consequences, critique[J]. Big Data&Society, 2014, 1(2): 205.
蒲清平, 范海群, 赵楠. 基于大数据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7(5): 22-24. 谢玉进. 近十年来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及其展望[J]. 科学社会主义, 2018(5): 149-154. 李超民, 邓露. 近五年来国内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述评[J]. 求实, 2017(4): 13-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31108
- HTML全文浏览量: 5727
- PDF下载量: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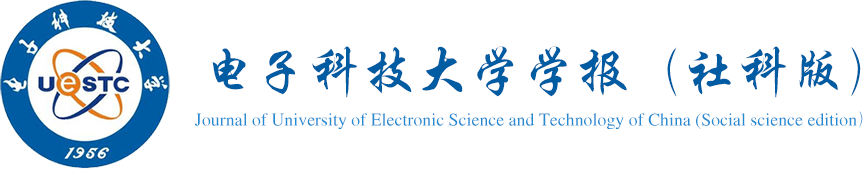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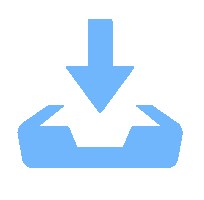 下载:
下载: